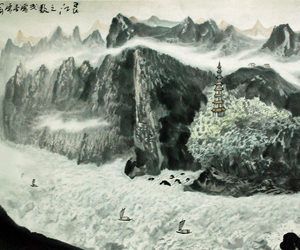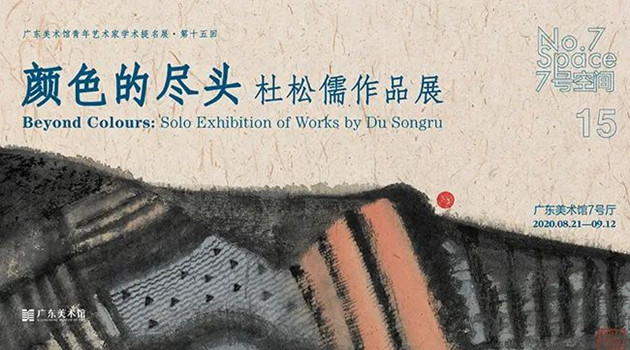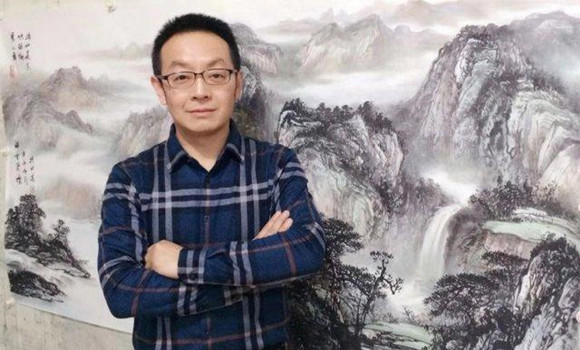|
莫晓松 : 逸笔傅彩 神韵横生
【袭古创今——画家莫晓松】莫晓松,北京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北京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全国美展评委。
中国画的精髓是一种文脉的延续,这么多年,我创作了不少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一直修正自己对艺术的看法和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书和画的关系到底在哪里?我收藏了一批彩陶,这些彩陶至少都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彩陶的画面、线条质感很强,这些彩陶图案是一种文字符号,也可以说是一种绘画,它既有抽象的、又有具象的,彩陶代表新石器文化那个时期的经典之作,是我们文化最开始时期的杰作,这个里面的艺术养分特别丰富,由此,我就想:中国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源泉在什么地方,那种蕴含的精神含义在什么地方?
青铜器上的鸟兽造型,艺术鼎盛时期,唐、宋的花鸟绘画作品,再去欧洲各地博物馆看看,不去比较,看不出来,西方艺术对人的刻画,非常精妙,但是,对自然的描绘,远远不够,花卉、自然意境等身边的景物,根本没有涉猎,远远达不到中国绘画这么深的层次,所以我觉得表现山水、花鸟的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中国花鸟画走进我们视野的那部分,就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徐熙、黄荃两座高峰,直到今天没办法超越,尽管我们现在有先进的摄影技术对造型可以更加细致入微,但是它基本的表现方法,丝毫没有突破唐宋画家对花鸟的描绘,在北京画院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思考的方向。
我一直在学习、吸收唐、宋代传统绘画,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很多印刷唐、宋花鸟画册,对黄荃的作品充满激情,喜欢他这种繁杂的制作过程,美轮美奂、精彩绝伦画面,觉得它好,把它放的很大,近距离的反复观看、反复临摹,自己可以临摹的很像,那时,我认为画面精工细致,线条的圆润流畅,这就够了,相反,我对徐熙的作品是一种朦胧的理解。随着这么多年在绘画过程中摸索,对彩陶这类艺术研究的加深,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才发掘更深层次的内涵,徐熙他以工笔的形式表达写意的精神,用"水墨淡彩"予人以超逸清雅的感觉,那种线条的表现力,让我的工笔绘画之路发生了改变,尽管徐熙、黄荃等唐宋名家名作,我临摹的很像,但总是无法结合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只停留在临摹,书写性,顿挫感、力度感难以表达,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去研究,总是觉得隔着一层纱,看不透,后来到了北京画院有很多机会和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一块写生或者出国考察,亦师亦友的袁运甫先生给了我一些启示,他说:“晓松,你应当找出一些好的作品,再找一些别人研究的文章进行对比,再结合自己创作特点,可能会有收获”。这么多年,大量查阅前辈对唐、宋绘画的研究成果,结合我的创作、我的写生,通过线条和画面的理解,揣摩历代名家渲染立意,弄明白画意在何处,以及他们的观察方式,古人的观察方式与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我们可以用照相机把所有的细节都拍的很清楚,古代画家只能通过眼睛,目识心记,从内心生发情感,变成一种“心我和一、物我两忘”境界,慢慢把这些理解融会贯通,现在,我觉得唐、宋绘画我能深入进去了,知道他们不足之处在什么地方,好在什么地方,我能学的在什么地方,懂得了这些方法,我觉得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只是觉得很好,说不出所以然来,不能理解作品背后的一些人文精神和一些文化内涵,现在,看到一张画我都能体会到一种中国文化的精神含义,通过画面也能体会到当时画家的精神状态和文化发展的脉动,我带学生的时候,尤其上大课,一次讲三、四个小时,山水、花鸟通讲一遍,触类旁通。
文人画,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苏东坡,他是中国绘画的强力介入者,加进去了很多文人的因素,他有很著名的一句话“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就是画的太像就和儿童一样了,影响至深,“文人画”就成了苏东坡的一个符号,中国画就此转向写意性和关注文人精神。当代中国绘画,尤其是工笔画,确实缺少了一种文人的气息,其实艺术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写意的,是表现精神层面的,不是表面的反应,而是要深刻反应人的思想、境界。好多人觉得工笔画很难看到画面以外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大家都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形”上面,都在比像不像,而缺少一种意境,一种写的精神,另外还缺少一种文化与心性的结合,而古人绘画,比如像明代陈洪绶,他把人画的高度变形,线条像刀刻斧琢一样,极度刻画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他的绘画技法适应不同题材,如用折笔或粗渴之笔表现英雄、细圆之笔表现文士美人、用游丝描表现高古,成为传统人物画法的丰盛宝库,相反,如果这些写意精神缺失,作品无论有多么像也不如一张摄影,西方近现代绘画之所以有消亡之感,就是太刻意于写实绘画这个方向。
我从西北来到北京,一直都有一种天地悠悠的这种情怀,尤其是在北京画院时间待长了,愈发觉得仅仅细致刻画根本不够,还要在线条和诗情画意方面修炼,我最初学画以人物为主,工笔非常具有写意性,但总觉得自己受的制约比较大,为此,这些年一直在汉隶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发现汉代的文字质朴又有气度,通过研习书法文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质朴精神,通过把书法线条运用到作品之中,增加作品的厚度,比如我的这幅《荷塘逸趣》先用泼墨的方法泼出一种氛围,然后再画几只鸟,表达天地之间的博大和鸟的点睛致微,表达生命的生生不息,按照宋人黄荃的画法,把鸟画的很具体,同时加上我自己的理解。
绘画,我目识心记的时间较多,对形的理解比较自由,我经常指导学生临摹,学生临了一遍和我过一遍是一样的,不停的看,既看到学生的优点,也看到他们的缺点,学生临,我自己看,虽然,我不面面全临,但是,他们不对的地方我会注意到,他们临的好的地方,他没注意到我先注意到了,我先学到了,在我指导他们这个过程就像我自己临了一遍一样,所以我学的可能比他们都要多,这也是自我吸收的过程。最近五、六年,每天四点起床临字,主要临汉隶,如:《张迁碑》、《西狭颂》,一个字一个字复印好,放到桌边,不像别人那样只临个大概,我是一笔一划,争取完完全全对齐,一天最少四、五个小时,到底能不能在书法上有点成就,我不好说,但是现在真的很享受书法给我带来的乐趣。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只是盯着一个点,很难达到很高的境界,一定是要从多方面研究,视野要宽些。我对彩陶也很喜欢,又对汉代的艺术比较痴迷,我的工笔画思路又不仅仅局限在黄荃和徐熙那里,但是,我以黄荃、徐熙作品为基础,把彩陶与汉代的文化精神融入我的作品里,效果就不一样了,我的院长王明明经常说:“晓松,一定要传统一点,你给我看有种当代的感觉,千万不要给我出现当代的意味”,其实我天天在看传统的,但是我画出来的比较现代,虽然我和王明明院长画风差异很大,但是我们俩近些年合作过很多作品,既有写意画,又有工笔画,风格相互融合,其中有八米乘十几米的大型创作,由于创作的地方小,我们就跪在地上画,很多次,王明明院长从早晨一直画到天黑,我从院长那里不仅学到了严肃认真的绘画态度,而且借鉴了很多他写意的绘画风格,要不是说我的工笔最近很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哪怕是我几个月完成的,最后有一股子气的力量,我的这种带有写意性的作品和其他的工笔画家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我的作品有一定的概括性,有些地方我会放弃掉,有些东西我要强调它,通过线条表现极端的方式,照相机表现出来的可能就不一样,我的线条表现既可以大刀阔斧,也可以用粗笔形式,也可以画工笔,我也用粗笔来画工笔,粗笔但是要经过细染,形的转化完全就是自己对形的感悟和那种通过照相机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也去用照相机,但是我是用照相机来启发我们的兴奋点,增强记忆的方面,而不是成为全部。有很多画家,画了一辈子,他的形越画越差,而有一些人物画家真正画的好的,比如黄胄,他根本就不用照相机,他把那个形态、精神和规律掌握的很好,他随意画出来的东西形都会很准,他从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整个人物造型画出来,说明他把人物的结构和形体掌握的非常准确。我这么多年对竹子的观察也很细致,只要有人说到竹子,我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结构,生长规律,长的过程,枯萎的样子,全部印到脑子里了;花也是这样,有时候去看荷花,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去看早上的荷花、中午的荷花、晚上的荷花,观察它到底有什么不同,把这些东西记得特别清楚,这些规律和过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创作的作品比照相机来的真实、来的生动。 |
 腾讯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 网站地图
网站地图 手机站
手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