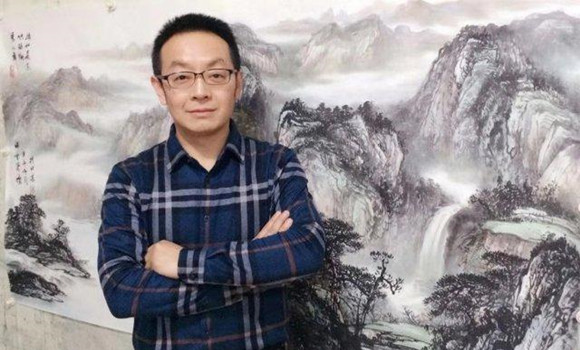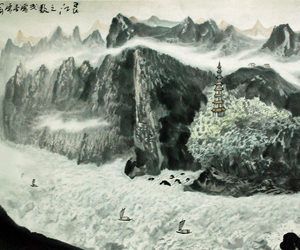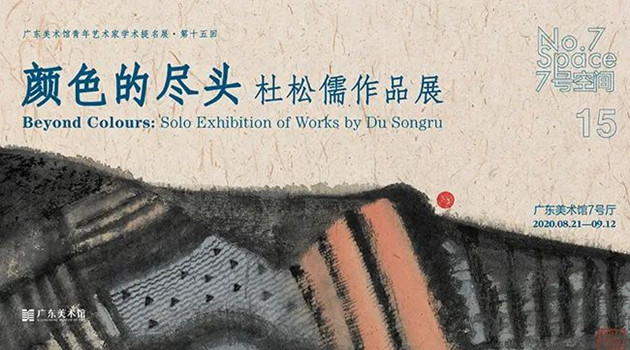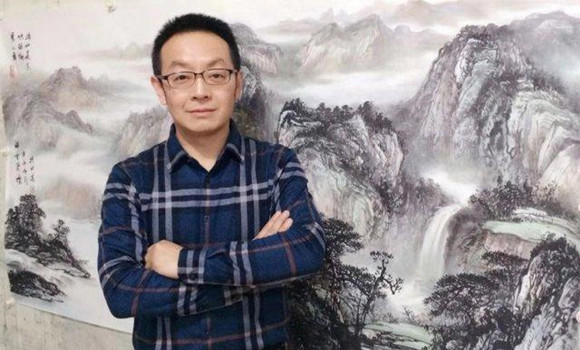|
上苍的安排,似乎注定苏百钧要成为最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 他出生在发祥岭南盆景艺术、有千年种花历史的广州花地,从小生活在馥林花园,加上祖上八代种花为业,父亲是花鸟画家和园艺家,自己早年还回乡当过知青花农,真可谓一身浸润于花香鸟语、翰墨丹青的世界,有着得天独厚的成才条件。然而,世上没有不学而知的天才。苏百钧令人景仰的绘画艺术成就,得之于他以守正且超然的自为之力,将人生机缘的或然化为必然。
自为之力的守正,在于其为学为艺,一路恪守中国画学正道,不曾追风逐巧,借端革旧维新而以旁门外道规避国画修为的必历之艰。国画修为从来需要经久磨砺,而之于讲求笔精墨妙的花鸟画功夫的养成,其艰难程度则甚于一般。晚唐以来,花鸟画赓续不断,从容精进,以曼妙绮丽之美尽展中华文化的优雅情致。回望历史,花鸟画坛巨擘辈出,遐迹或工或意,法度谨严,技艺精湛。其堂堂之成,如高山峨峨,若大河汤汤,叹为观止。对于当代花鸟画家来说,这煌煌之史成既是师学借鉴无比丰富的典范和宝藏,又是建树自我难以超越的经典和高度。苏百钧的父亲苏卧农,凭其作为杰出岭南派画家的非凡识见,一开始就引领他走上攀登艺术高峰的艰难正道。父亲循循善诱的家学教育,让他听说读写、练手辨眼、动脑用心、身体力行,从小打下扎实、全面的艺文修养功夫。自立之后,他始终坚定自持,卓尔不群,虔敬正诚地循主流正途,默然苦修传统功课,对中国工笔花鸟艺术的经典厚积,研精究微,广采博取,坚忍不拔地缘遐迹文脉探寻艺道堂奥。长期以来,他远师宋元,近承岭南,始终不愠不躁地思考画理、锤炼笔墨、推敲章法、琢磨技巧,殚精竭虑,用功极勤,以至汲得大成自我的百家滋养。
自为之力的超然,在于其为学为艺,始终戒忌唯古是从、泥古不化,不曾为尊重传统程式而拘囿己心、僵滞不前。苏百钧天资聪颖,总怀关心、好奇于生活日常,善以豁达活泼、细锐敏感的诗心,体察感悟自然生态的蓬勃生机和倏然情状,善以体贴内心情思的手法变化和丰富技巧,将感通于时景时气、时禽时芳的生命节律和神情意态融变为绘画语言,让笔下形态焕然开新。他遵父亲“养以发真,悟以入妙”的教导,缘心性蒙养造就“激于中而横于外”的识见灵气,以至能够迁想妙得、举一反三,不流于见槐是槐、见柳是柳,为成规实事所拘囿。苏百钧之所以能够苦修传统功课又不至于泥古不化地保持难得的超然之力,很重要原因在于他十分重视写生。在他看来,写生是画家与自然之间的心灵沟通,通过写生可以“清空自我的固化经验来认知、体悟和捕捉自然界的新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自我美的程式。”对他来说,“观物取象”的写生过程是“度物象而取其真”的审美认识过程。这一过程通过感受客体的内在活力、体验自身的情感变化,以至纳宇宙生机于胸底、发人生价值和人文精神之感悟,最终将物象转化为“物我相契”的心象,达到“物我两忘”的审美自由,使画家从程式习惯中跳出来,实现对现实的创造性把握。正因为重视并坚持写生与创作接轨,他的工笔画总能保持新颖之貌和清雅之质。 为学为艺,修身为本。一身于苏百钧的守正与超然,透着端正的态度、取向、姿态和作风,透着对生活与艺术、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正确认识。遵循正道、正身诚意的修为功夫,造就了苏百钧全面的人文修养、深厚的专业功底和超强的创作能力。这一切激发出他的旺盛艺术创造力,也造就出情深、意切、趣足的高致艺术。 发乎生活的情感是艺术创造的基础,充满感情的语言是艺术感染的条件。苏百钧重“情”,强调艺术创作“就是要反映令自己感动的东西”。他有诗人一般的情怀,审美感觉敏锐,善从自然中发现和捕捉触动心灵的生动细节和瞬间。对他来说,但凡落笔入画的,必是首先打动己心的,无论素材处理、题材选择或是主题把握,皆以真情实感的“合情”为根本。譬如,苏百钧说他爱关注各种荷莲的生长过程,每年荷花盛开之时都会到荷塘边游赏或写生,以至对荷塘、莲花的认识与日俱增。然而,即便有这样深的认识基础,即便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有意画一幅风动荷叶的场景,却因为“迟迟未曾寻到有力量的情感共鸣,只得暂且搁笔。”由此可见苏百钧重“情”的程度,而他的《早春》《仲春》《昨夜风雨》《秋荷》《秋荷二》《秋塘野趣》《愁绝水一方》等作品都这样创作出来的。渗透形式结构深层或基底的真挚情感,化作曼妙而蕴藉的画面情态,予人以深沉的感动。
仅凭情感宣泄,无以进取艺术的髙致。真正的艺术创造力离不开思想,不能缺乏对生活的理性认识。苏百钧深谙艺术规律,了悟艺术表现的根本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思想情感或理想情怀,以至一再强调“意是工笔花鸟画的灵魂”。他“度物象而取其真”,由自然景物感发体贴人生哲理和理想的心象,并缘之为经营构图、造型、线条和色彩的意匠,让形式饱含意蕴,让形象超越物象,最终达到审美意象的充分表达。《追忆的故园》是苏百钧获得“首届中国重彩画展览”金奖的代表作。作品描绘了台风过后的场景:大片芭蕉被摧折,林间雾气弥漫,白鹭似乎迷茫地寻觅着什么……风灾后的故园狼藉一片,然悲怆中却见倒伏的片片蕉叶都在倔强地往外冲。这被作者着意刻画的新生命开始的迹象,实质是比附于大自然新陈相继、生生不息之情状的人文精神的张扬。对这幅作品,他做过这样的陈述:“人和自然的对话不能逃避情绪的浸透,艺术源于个别自然,应以它为原形。然而远非如此简单,许多艺术要背离自然,有别于自然。创作就是要反映令自己感动的东西,一切真正创造性的努力都是在人的心灵深处完成的。绘画是经由真实想象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绘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思维的过程,是用构图、造型、线条和色彩等进行思维的过程。绘画艺术独特的词汇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顺应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被连接起来,形成了合乎艺术自身逻辑的‘绘画语言’。”在苏百钧的画作上,表达生活理性认识的“合理”要求,化作有意味的形式和以思想灵魂挺立的形象,构成发人遐想的“象外之意”或“象外之境”。 艺术的高致境界,既在于“合情”,又在于“合理”,更在于情理交融的“有趣”。“趣”,是艺术家主观意旨通过一定艺术手段而表现于作品的独特风致、情趣或意趣,是在艺术欣赏中能给人以美感的一种审美属性,也是审美追求所期望的艺术境界的极致。苏百钧绘画的高致性,在于它十分“有趣”。譬如,其经营构图,取景片段的“不完整性”,带来画面气局蓬勃豁然的生动感;其描绘物象,渴笔疏线的“不连贯性”,造成笔法线型气贯势畅的韵律感;其落墨敷彩,撞水撞粉的“不确定性”,赋予质地肌理难以名状的新奇感……所有这些“趣”,或发显宏阔,或透露幽细,都是由虚实聚散、轻重缓急、干湿浓淡、厚薄冷暖等辩证品性纠缠创化的形式美感。譬如《雨霁》 一作,巧妙地采用“没骨”与“撞水撞粉”技法处理,把干裂土地雨后散发水气的特有湿润感觉表现得恰到好处,而这种意趣的表达是无法诉诸宋人勾染法的。如苏百钧所言,“那环环相扣的纹理,淋漓渗化的墨、色以及难以名状的意趣,无不给人一种新奇的美感。画面上斑斑驳驳、强弱不一的墨色,通过点、线、面的形状极其自然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干湿浓淡虚实聚散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节奏和韵律。”它们作为传情达意的托迹,于情理交融中呈现风格形式难分具象抽象的生动性。这些已然摆脱描形状物之被动而显示画家创造性的绘画形色质,构成浸润苏百钧画作的卓然审美价值。 凭借守正和超然,凭借情之深、意之切和趣之足,凭借明丽典雅、清幽杳渺的画境和神遇迹化、超于象外的盎然意趣,苏百钧工笔花鸟画艺术如俨俨高峰超拔于当代画坛,堪称艺术创作正道高致的表率。 |
 腾讯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 网站地图
网站地图 手机站
手机站